【本文导读:在人类社会各种各类组织富勒姆主场击败对手,取得胜利的管理行动中富勒姆主场击败对手,取得胜利,组织的文化是最让人捉摸不住的存在了,管理这个存在很让人头疼,但做着管理和领导工作的人们又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因为也许是你米兰体育正在无视它的那个时候,它正在发挥着致命的作用,制造着加速胜利或者快速灭亡的最后一个事件。~这就是文化,一个组织里的人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继承下来的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思维以及行动方式。
自大战略的角度去考量,组织中的文化当然必须估计以及顾及到,因为这是组织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心理资本,它或者让组织产生希望乐观自富勒姆主场击败对手,取得胜利我效能以及韧性,或者可能令组织不断地生产出失败主义的东西~~~
当前,我们文章中的北宋朝正在经历这个要命的过程。王朝是建立在唐末五代十国的基础上,而这所谓的五代十国都是由唐帝国末期原来那些尾大不掉的节度使~他们之中的有野心者建立的,甚至这种节度使的野心进一步鼓舞起来的同样有野心却级别更低的军官们杀掉自己的上级窜立的,这些由军官们甚至下级军官建立的素质很差的王朝政权在华夏中原原来大一统的帝国地面上相互攻杀争夺,时间久了为了生存和胜利不免生出一系列的战争规则,一些特别有割据政权特色的规则。宋王朝的开创者赵匡胤集团正是这个特殊时期一样的方式赢得政权的篡夺者。而他们也正是继承这些华夏中原军阀混战的某些胜利规则的身怀者。
问题是,这种中国历史特殊时期形成的战略文化不具有普遍性,而且时代以及时代条件总会在变化,因此,运用这些特殊时期的战略具有极大的风险,如果五代十国的军阀头目们中间有一个是明白的人,就必定会看破这一些,并且适时地坚决地予以改造,我们必须遗憾的是,当前的大宋王朝皇帝赵匡胤或者是这个遂行改造的人,但是他不合时宜地死啦,他的继承者宋太宗赵光义不是,就如同其他那些五代十国的所有篡夺者一样,没有改变这些战略文化的主观条件,按照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钱穆的论断,这些走马灯式轮换的皇帝们大都是一些下级军官~赵匡胤的品阶还要高一些,本来就是军阀而不是政治家或者军事家,素质低下,不可能有改变战略文化的能力~~~
中华民族在宋朝的路口上,注定有几百年的蹉跎岁月!】
内政导向与野战取向——北宋朝有这个难以解决的巨大矛盾冲突
核心内容提要:北宋经略幽燕期间,不同层次的战略文化取向存在落差,虽然在大战略的层面,宋初文臣大都主张先稳定内部统治,巩固民生,再从事对外经略。可是这种规范并不能有效地整合五代遗留下来的军事信念和组织文化。
北宋朝经略幽燕期间的据对依然承袭五代以来崇尚野战的传统和急速的军事节奏。这令宋军在一旦使用武力时倾向于快速突击,及对准敌军中心,发动风险偏高的决定性战役,而未能在持久战中发挥社会稳定及经济较为繁荣的优势。
战略文化
战略文化是一种孕育于19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学术观点。1970年以前的绝大多数战略学家都相信大战略是最高层次的战略,柯林斯在1973年的《大战略:原则与应用》一书中提出,大战略的定义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等因素之外,还包括了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信仰习惯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方面。
自1970年代后期,杰克·斯奈德正式使用战略文化一词,就试图探索大战略更深层次的文化信息,而这个文化信息如果单单放在大战略层次是看不清楚的。
这一时期的战略文化学者强调了战略文化是一种行为典范,去为大战略取向作出指引,这个典范由对使用武力效益的评价、对使用武力频度的评估,及对冲突的零和性质的评估三个指数构成,如果三个方面的数值都很高,则表示了该国很可能会使用武力解决纠纷。
由于不同的军队、军种甚至团队各有其独特的成功经验,这种经验会模塑为军事信念,影响着未来从事战争的方式。战略文化对不同文明和国家的暴力观也具有独到的解释能力。由于战争是政权之间合法使用暴力的状态,在哪种情况下容许使用暴力,不同的价值体系做出不同的答案。
虽然中国传统思想时常提到“义战”、“非攻”、“观德不耀兵”,但只能算是理想政治的产物,作为“象征战略”——将军事攻略合理化的政治托辞而存在,与战略实践毫不相干。学者围绕儒家有限度使用武力的规范展开讨论,观察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否得到贯彻,象征战略与现实战略之间所产生的脱节现象,是透过“权变”为核心的一系列文化规范不断的协调,令两组本不能共存的战略取向得以并行不悖。
宋初986年以前的战略文化存在高位和低位的落差。在高位而言,文官政府尝试对武力的使用赋予一定的规范,防止其被滥用。在大战略的取向上,文臣如张齐贤、田锡、赵普等都力持内政优先的主张,意图是防止兵连祸结,令人民生计陷入困苦,最终危及王朝稳定。这种内政主导的大战略反映在“先本后末”、“安内养外”的观念上,反映了渊远流长的儒家政治观点,认为“民为邦本”,勤于内治是远夷柔服的先决条件。部分观点更认为内部秩序稳定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资源,可以转化为军事动力。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以上战略取向只反映高层决策受到文官政府的意向影响,而军队内部却承袭着五代的传统而呈现不同的取向。五代北宋之际的军队中存在着另外一种规范,标榜个人武艺和勇敢行为,具有鲜明的野战取向。在战役法上,热衷于野战的宋军采用了弹性防御的模式;当转取攻势时,则偏好运用突然性和使敌人措手不及的纵深攻击。这些规范的形成与五代的新近经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了战略文化的延续性。
这两组规范虽然不对称,但并非完全没有协调的空间,在一般情况下,大战略仍然规范了战役法,军人纵使好战,也不能畅其所欲。
可是这个规范并不全面,一方面,内政主导论者为使用武力预留了空间;另一方面,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偏见常常夸大了敌国的内部矛盾,为机会主义的登场铺平了道路。基于这些困难,统治者并非时常都能找到适合的人选去进行战略协调。更值得注意的是,两组规范都同样反对持久战,这也解释了经略幽燕期间的宋军,为何一旦动起武来会企图速战速决,而非像宋夏战争那样倾向于繁复的进筑城寨作业。
北宋初年对战争和战略的文化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以传统的价值观达成对暴力施以制约傻瓜。价值观作为文化的一个主要方面,起着对暴力的本质及如何使用暴力的定位功能。当然,这种对暴力的反思,主要在于如何防止滥用暴力,而不是彻底反对使用暴力。
因此,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986年以前的弭(mi)兵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内政导向的大战略。它的内容不只是弭兵,而是协调内部统治和国际竞争的大战略。其理论根源,来自儒家的“民本轮”,及两汉朝臣对此的一些发挥。论者看到帝王穷兵黩武的负面结果,以及战争对民生的破坏,因此他们对帝王使命的建构以内政的稳定为优先,而收复疆土,耀兵塞外,只是内部安定的结果。他们界定内政的利益特别是以人民的生计为重,因为人民的生计涉及国家的后勤力量。当后勤力量变得脆弱时,朝廷也自然就没有能力进行东征西讨。
内政导向的大战略从宏观的角度观察,看到战略资源可以相互转化。人民的支持,粮草的储积都可以转化为军事动力。如能先稳定内部,在长远的国力竞争中,宋人可以占有上风。“先南后北”的战略结构就带有这样浓厚的意味。内政优先的取向,固然不反对使用暴力,但却防止了滥用暴力。
宋初的帝王通过弭兵论建构自我形象,可以看出他们身份认同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宋太祖、宋太宗在不同的场合都批评过后唐庄宗这位五代中武功最高的帝王,显示着他们极力要和五代划清界限——他们看不起五代时其余那些出身卑贱的帝王们,要想办法跟他们划清界限。宋太祖很关注后唐庄宗“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却不能用军法约束部下的教训。宋太宗则直指“庄宗可谓百战得中原之地,然而于守文之道,可谓懵(meng)然矣”。他又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以文德致治”,反映了他们不甘心循五代的旧轨,而决心致力于内部安定开创新局。
在这种思路之余,就出现了汉武帝、唐太宗皆不足法的论调。田锡认为“汉武帝躬秉武节,遂登单于之台,唐太宗手结雨衣,往伐辽东之国,”完全是得不偿失。
循着这一路向,张齐贤高唱“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的经验,并歌颂宋太宗“真尧舜也”。连宋太宗在下弭兵之诏时,也引用老子“兵者不祥之器”自况,以古人的智慧作一番感兴。从这里看宋初帝王对自己的角色认同,以及文臣对帝王形象的构建,都力图与上古盛世接轨,而摆脱五代的阴影。
与此相应,不论真实的情形是多么不堪,这些文臣也将自我角色自以为是地定位到太平盛世的名臣,尽管其实相去甚远,根本无法同日而语。据赵普所言:内政主导的大战略可以追溯到汉、唐,他们看不起汉、唐的成功,因循着失败、再失败、彻底失败和掩饰、再掩饰、彻底掩饰的虚无主义路线,然而却曲折地反映着一条角色认同的轨迹。
战略文化的纠结:五代军队的野战取向
宋初军队的野战取向,来自于五代尚勇好斗之风,本来是军事生态学上汰弱留强机制的产物。军官的选拔凭的是个人武艺,这反映在宋代军队排连和堆垛子的制度。加以作战中军功的晋升,也要凭借该作战单位获得首级的多寡而定,这令军官与其所统辖的士卒有荣辱与共的关系,崇尚武艺也就成为军队中的一种集体的组织文化。
胡族血统及其所濡染的文化传统,也是军队中好勇斗狠风尚的来源。李克用的沙陀军来自漠北,“(后)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倶皆一时雄杰虣(bao)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其中李嗣恩是吐谷浑人,李存信出自回纥部落,李嗣源小名邈佶(ji)烈,后来做了皇帝,也自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还有很多所谓“代北人”,正史的传记中,没有记载他们的族属,但相信也可能是迁徙至内地的胡族之后,或者是胡汉混种。如李存孝“代州飞狐人也,本姓安,命敬思。”安重荣小字铁胡,朔州人,安从进,“振武索葛人也。”宋还有党进、呼延赞、米信等边疆民族的将领。至于著名的府州折氏,也具有胡族血统。
五代的军队中标榜个人的武艺与勇敢,表现为斗将的现象。在李克用的沙陀军中李存孝是以勇猛见称的,连朱温阵中素称骁将的邓季筠,也被存孝舞矛擒之。来自山东的夏鲁奇,最好斗将,征伐幽州时,常与刘守光部下单廷珪、元行钦单打独斗,两军士卒“皆释兵而观之”,出现古典小说中常见的斗将场面。梁末独立支撑大局的王彦章(862—923),也是被夏鲁奇“单马追及,枪拟其颈”而就擒。可是铁枪王彦章也是大名鼎鼎的勇将,“为人骁勇有力,能跣足履荆行百步,持一铁枪,骑而驰突,奋疾如飞,而佗人莫能举也,军中号王铁枪。欧阳修就写过一篇《王彦章画像记》,记载他的英雄事迹如何为乡里小儿所传颂。
即使是契丹入侵,也未能使中原的猛将失色。符彦卿、高行周都以擅野战闻名。唐庄宗被乱兵所杀,符彦卿、王全斌和何福进等十余人激战至最后一刻。阳城一战,符彦卿横领万骑冲辽军大阵,而令契丹人丧胆。契丹人每逢马匹生病不肯进食,“必唾而祝曰:‘此中岂有符王邪富勒姆主场击败对手,取得胜利?”当述律太后知道耶律德光从中原撤军,而没有带同符彦卿时,也失望地说:“留此人中原,何失策之甚也?”
崇尚武艺的军中文化,使得谋略之人不容易取得军中的认可。周德成本来属于比较有谋略的将领,“常务持重以挫人之锋,故其用兵,常伺敌之隙以取胜。柏乡会战,李存勖靠他的以逸待劳之计击败了王景仁。可是他却也时常卖弄武艺,曾舞檛(zhua)擒“陈夜叉”、单廷珪等猛将,后来做到幽州节度使时,也“恃勇不修边备”,导致契丹的入侵。
何时需要谋略来解决问题,何时不得不逞匹夫之勇,在周德成身上好像看不出一个行为规律。这反映出一个有谋略的人处身在尚勇好斗的群体中角色认同的吊诡。相反,凡事都采谋略为主导的角色,却不容易得到众望。刘鄩(xun)(857—921)算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师承《六韬》,“涉猎史传”,用兵以奇变为主,“一步百计”。他凭着智取兖州,一战成名,后来不得已降梁,穿着一袭素衣,骑着一口小毛驴,充分呈现儒将本色。可是在决定性的魏博之战中,他上为梁王所疑,下亦不被众将所服,因此有“一杯之难犹若此,滔滔河流可尽乎”的感概。在李存勖的眼中,刘鄩(xun)“长于袭人,短于决战”,欠缺了一分过人的胆色。
由后唐开始,注重勇武的风尚影响到军事领袖的身份界定,他除了要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决策者之外,还必须是一名武艺超凡的勇士。这两种身份之间潜藏了矛盾,经常参与白刃格斗提高了战斗风险,将个人生命作赌也可能令苦心策划的战略付诸流水。可是在沙陀军中,战斗似乎是一名军事领袖值得承担的风险,否则他很可能不具备作为领袖的资格。李存勖的一生印证着这个身份认同的历程,也被塑造为个人英雄主义者。他早年颇具战略眼光,曾劝李克用摈弃小怨,与叛将刘仁恭合力拒梁。可是当他继位时,周德威,李嗣昭等大将都拥兵在外,他唯有力战以树立个人威望,“十指上得天下。”“帝锐于接战,每驰骑出营,(符)存审必扣马进谏,帝伺存审有间,即策马而出,顾左右曰:“老子妨吾戏耳!”明宗李嗣源也是一个典型的斗将,他批评诸将“公辈以口击贼,吾以手击贼”,其率领的“横冲都”威名远播。在讨刘守光一役,他单挑元行钦,七次射中对方,而“行钦拔矢而战,亦射中明宗中股”。在917年救幽州一役,为先锋的李嗣源高呼要和耶律阿保机角力。明宗的义子王从珂和女婿石敬瑭都胆色、武艺过人。李存勖曾称赞从珂:“阿三不惟与我同齿,敢战亦相类。”石敬瑭曾经凭过人的武艺,在重围中救出李存勖,因而得到啗(dan)酥的荣誉。啗(dan)酥,夷狄所重,由是名动军中。
到五代末年和宋初,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一些转变。周世宗没有沙陀血统,对于白刃格斗也开始不感兴趣。宋太祖重新界定君主作为战略策划者,而非战斗参与者的角色。他用师荆湘,既取西川,都只是居中策划,没有参与军事行动。可是对于关键性战役和敌人,如北汉和辽,他们都是一再发起亲征,还常常参加战斗。周世宗亲征高平,“自引亲兵犯矢石督战”,丝毫不敢退缩。宋太祖水灌太原一役,亲自指挥水军乘小舟载强弩进攻其城,扈从的禁军将校王廷义、石汉卿皆中箭镞死,反映了宋太祖尚未脱离开五代的组织文化。宋太宗在高粱河遭辽军击溃,多年后却大言“往则奋锐居先,还乃勒骑殿后”,未尝不是五代风尚的一些余波。
纵使后周和北宋对皇帝的身份认同开始向中国传统回归,军队中对个人武艺和胆色的崇尚依然持续。宋初的党进,就具有边疆民族血统。他在982年围攻太原一役,击败了“素称无敌”的杨业,令后者要缒城而上获免。后来辽朝使者还专门问到,像党进这样勇猛的将领还有多少?呼延赞也是一位武艺高强的将领,他“挥铁鞭、栆槊,又作破阵刀,降魔杵,戴铁角巾,“两旁有刃,皆重十数斤。稍后成名的田敏(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也是武艺出众,唐河之战,“敏以百骑奋击,敌惧,退水北,遂引去。”1000年,田敏在北平寨附近袭击辽军大帐,令辽圣宗留下深刻印象:“问(萧)挞览曰:“今日战者誰?”挞览曰:“所谓田厢使者。”契丹主曰:“其锋锐不可当。”遂引众去。
总之,个人武艺作为带兵官的一项身份认同,一直是宋初军队组织文化的一部分。
随着宋初集权统治的加强和强调军纪的重要,宋太祖和宋太宗提拔了一些能够严格执行纪律、而不突出个人英雄主义的武将。这种措施为宋军的组织文化带来新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典型人物是曹彬。
曹彬不像其他武将那样好结交,品格中正不阿,为人廉洁,因而得到宋太祖的赏识。王全斌伐蜀一役,诸将多受贿赂,军纪大坏,只有曹彬保持廉洁。后来太祖取南唐,太宗经略幽燕,都以曹彬为主帅。曹彬对宋军的战术和战役法缺乏建树,但他身体力行,讲求仁厚、廉洁、奉法的为将之道,与儒家的礼仪伦常,建构了一道相容空间,令他的将业在宋初享有崇高地位。田重进也是一个廉洁而低调的人。他在太祖末年很多军官都收受晋邸的礼物时,断然拒绝同流合污,讲:“为我谢晋主,我知有天子矣。”后来宋太宗当上皇帝,“爱其忠朴”对他青眼有加。田重进事实上颇能打仗,第二次幽州之役,就只有他的那一路屡战屡胜,而又全军全身而退。崔翰虽然属于有谋略的类型,但他同样不标榜白刃格斗,而着重维持军纪。“翰分布士武,南北绵互二十里,建五色旗号令,将卒望其所举,以为进退,六师周旋如一。”宋太宗就认为“晋朝之将,必无如崔翰者”。王超也是一位讲求整齐划一的排阵专家。在999年的一次校阅中,他手执五方旗,能令二十万的大阵进退自如。“步骑交属亘二十里,诸班卫士翼从于后——初举黄旗,诸军旅拜。举赤旗则骑进,举青旗则步进。每旗动则鼓駴(hai)士噪,声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举白旗,诸军复再拜呼万岁。有司奏阵坚而整,士勇而厉。”在澶州之役中,他指挥的定州大阵的去向,曾被认为举足轻重。宋太宗和宋真宗在藩邸的时候,都各自培养了一批谨厚而奉法的军官,他们对宋初军事力量的组织文化之影响力不可低估。
讲求服从命令,减少突出个人的组织文化,和五代遗留的英雄主义传统很容易产生磨擦,特别是在两次皇室继承权出现纠纷,衍生出激烈的派系斗争的时候更是如此。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新的组织文化之起着减少匹夫之勇的作用,并没有整体扭转五代以来崇尚野战的战役取向。两种取向的协调,出现注重结阵而战的取向。列阵既是强调团队的传统,也预设了野战的取向,相对是两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作战方式。当然要注意的是,在这里野战兼容了阵列,是作为守城的相对概念来使用的,即如周德威所谓的“镇、定之士,长于守城,列阵野战,素非便习”。这和后来岳飞(1103—1141)和张所(12世纪初)的野战全然不同。
宋太宗时期宋军多作前后两阵的部署。
宋琪曾经建议“前军行阵之法,马步精卒不过十万,自招讨以下,更命三五人蕃候,充都监、副戎、排阵、先锋等,临事分布,所贵有权。追戎之阵,须列前后,其前阵万五千骑,阵身万人,是四十指挥。左右厢各十指挥,是而是将。——阵厢不可轻动,盖防横骑奔冲。此阵以都监领之,进退赏罚,便可裁决。后阵以马步军八万,招讨董之,与前阵不过三五里,展厢寔(shi,停下来,止息),有常山之势,左右排阵分押之,或前阵击破敌人,后阵亦禁其驰骤轻进,盖师贞之律也。”
在满城会战、和陈家谷会战,宋军都采取这前后两阵的部署,前者获得成功,后者则由于天气恶化,李继隆后阵退兵而失败。宋真宗时期的阵型梯次更多,据《五经总要》所载,一组纵深梯次的方阵包含步骑十万人,大阵“常满十万人”,前后分别有约三万骑组成的前阵和约两万人组成的后阵,加以掩护,左、右两翼各有拐子马阵。相信这反映了宋真宗时代的情况。前阵之前一段距离,还有主要是骑兵组成的先锋队和策先锋阵,“遏其奔冲。”
崇尚野战的取向也反映在兵器的选择上。一般来说,射程兵器,特别是强弩,是五代和宋初的军队所倚恃的武器。晋出帝澶州之役,万弩齐发,飞矢蔽地,辽军无法突破。杨业在陈家谷战役时说过,他若败回,“则以步兵强弩夹击救之,不然者,无遗类矣”。在他心目中,因为陈家谷的特殊地形,步兵和强弩才是主力,足以对付辽军的追骑,以致他发现潘美撤走了这路援兵,立即附膺大恸。是什麽原因令步兵和强弩成为如此君子馆举足轻重的?君子馆战役也有类似的线索,当时“天大寒,我师不能彀弓弩,敌围廷让数重”。不能彀弓弩和败绩似乎存在因果关系,其实,多年后的澶渊战役,辽军统帅萧挞览也是中床子弩而死的,当时“契丹——抵澶渊北,直犯大阵,围合三面,轻骑由西北隅突进。李继隆等整军成列以御之,分伏劲弩,控遏要害。其统军顺国王)挞览,有机勇,所将皆精锐,这个时候是先锋的位置,这时宋军大阵中的威虎军头张瑰守着床子弩,暗暗施放,射中萧挞览的头部,辽军惊惧万分,欲逃走却不敢动弹。此役大名府的守将孙全照也以用弩手而驰名。这些案例都证实,宋军的强弩是对付辽军骑兵的主要武器。
另一方面,五代和宋初的军队对近身肉搏的战技是非常注重的。在928年的曲阳之战,王晏球命令骑兵全部丢掉弓矢,以短兵击之,回顾者斩,于是骑兵先进,奋檛挥剑,直冲其阵,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伤过半。
这种野战取向反映在防御战中,就形成了“弹性防御”。弹性防御是战略间接路线在防御战中的体现。它不直接保卫领土,而是采取机动作战的模式,以击败敌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保卫领土的手段,因此也称“机动防御”或“积极防御”。在战术和战役法上,弹性防御主张以一支能够迅速调动的野战力量为核心,透过迂回、遮断、夹击、包围等手段在野战中打击敌人的军事力量。宋太祖时北边曾经采用前沿防御,但自太宗起,采用弹性防御的个案大大增加。
在攻势作战中,五代的传统擅长运用突击,而这种传统具有经济、政治和地理因素。五代政权的经济基础脆弱,在长期战争中苦于支绌。923年唐庄宗渡河灭梁前夕,租庸副使孔谦暴敛以供军需,民多流亡,租税亦少,仓廪之积不支半年。后晋抵抗契丹,首尾三年,军储也是非常紧张。政权合法性基础薄弱,军队的士气波动很大也是一个重要的变数。五代的军队秉承河朔故事,“变易主帅,有同博易”,这种现象后来蔓延到禁军,出现“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的说法,只要首脑被推翻,其肢体也迅速瓦解。加以从地理上说,许多藩镇和十国的地盘大都比较狭小,防御的纵深有限,很容易被急速的突击所冲垮。
这些军事上的弱点却为奇袭的战略提供了机会。令奇袭成为五代军事传统中富有特色的方面。
问题是,奇袭是需要速度的,在速度的竞赛中,步兵集团为主北宋朝的军队远远落后于以骑兵集团为主的辽国军队。这就仍然是一个老问题:要不北宋朝局效仿汉武帝,缔造一支具有自己独特战法、与游牧民族部落不相上下的骑兵军团;要不就需要在整个国家与整个军队中,革新战略文化,创新战法,充分运用己方的优势,逐步探索削弱敌军优势的崭新战法。
我们当然已经知道了结果,汉武大帝是那个成功地实现战略文化革新的成功者;北宋的君主们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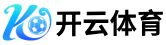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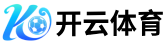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